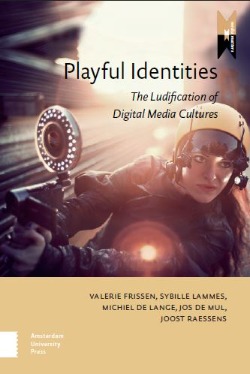约斯·德·穆尔. 游戏是哲学的真正官能———游戏本体论与谢林、赫伊津哈、博尔赫斯及其他.
n.b. This web version of the article is without footnotes. If you want the version with footnotes as published in Social Science Front, please download the pdf.
[荷兰]约斯·德·穆尔,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哲学系教授。
游戏是哲学的真正官能——游戏本体论与谢林、赫伊津哈、博尔赫斯及其他
这个世界,萦绕着游戏的幽灵。20世纪60年代,“ludic”一词在欧美流行起来,用来指代游戏性的行为和产品,游戏性日益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特征。在21世纪的头十几年里,甚至可以说是全球化的“文化鲁迪化”(ludification of culture)。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电脑游戏的巨大普及。但是,尽管计算机游戏可能是最明显的“鲁迪化”,但它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游戏性似乎已经渗透每一个文化领域。例如,在当下的体验经济中,游戏性不仅占据着休闲时间(乐享购物、电视游戏节目、游乐场、电脑和互联网或智能手机的游戏性使用),也成为过去那些严肃领域的特征,如工作(今天首先应该是有趣的)、教育(严肃的游戏)、政治(戏谑的竞选),甚至战争(像战争模拟器和界面的视频游戏)。根据Jeremy Rifkin的说法,游戏在文化经济中的重要性正变得如工作在工业经济中一样。后现代文化作为整体被描述为“一个没有总体目标的游戏,一个没有超越性目的地的游戏”,根据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甚至人类的身份也变成一种游戏现象,在鲁迪文化中,游戏性不再局限于童年,而是成为一种终生的态度,“后现代成年人的标志是全心全意拥抱游戏的意愿,像儿童那样”。
鉴于此,游戏和竞玩现象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例如,博弈论在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中的应用,除了这些业已存在的学科对游戏的日益关注以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休闲时间的大幅增长和鲁迪工业及鲁迪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新的领域也开始完全致力于研究游戏,特别是计算机游戏。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鲁迪文化”?它对21世纪初的生活和世界观有什么启示?我将借助两本书的分析对“鲁迪化”(ludification)现象做出解释:一本是弗里德里希-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另一本是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以下简称《游戏的人》)(1938)。此外还有一篇短篇小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La Biblioteca de Babel,1941)。若我们把这些作品放在以数据库本体为特征的计算机时代,它们将会在作为支撑鲁迪文化的游戏本体论问题上,为我们提供启发性观点。
文章前两个大问题讨论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和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思想,讨论二者共有的浪漫主义倾向:一是通过世界的审美化实现内在超越,二是二者对现代技术的厌恶。而与谢林和赫伊津哈的预期相反,他们所追求的游戏性本体论恰恰在现代信息技术中得以实现。第三个大问题将讨论《巴别图书馆》(也指互联网上对这个图书馆的游戏性模拟),结论是:技术的鲁迪转向使电脑游戏成为“真正的哲学官能(organon)”。
一、艺术作品作为哲学真正和永恒的官能
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1775—1854)不仅是德国唯心论三位主要代表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浪漫主义哲学家之一。尽管谢林哲学中的一些因素可以在康德、席勒等先驱(甚至更早)以及荷尔德林、路德维希-蒂克、诺瓦利斯以及奥古斯特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兄弟的思想中找到,但一直以来谢林是将这些哲学要素体系化的人。谢林的哲学经历过几个基本的转变,当深入研究鲁迪文化的基础时,谢林在1800年出版的《先验唯心论体系》则是最相关的文本。这本抽象的形而上学著作,感觉像本古书,要找到其研究进路,必须把它置于当时代,特别是要关注一些当时重要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因素。
1800年前后,德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由康德在其先验哲学中提出的,他批判性地分析了人类理性的理论和实践运用。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分析了理性的理论运用,提出了著名的哥白尼式转向。康德认为在我们试图理解世界的过程中,与西方哲学迄今为止的想法相反,我们的认知并不能符合对象,而是对象必须符合人类的认知。康德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并不否认人类思维之外“事物”的存在,但在其先验哲学中,他认为构成我们经验世界的现象(Erscheinungen),是“物自体”和我们直观的先天形式(时间和空间)以及先天概念(如因果性)的综合。我们所处的世界不是它本身,而是它在我们有限的人类认知中出现的世界。在因果决定的表象世界里,自由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分析了道德意志,或者更准确地说,分析了理性使我们的自然倾向服从于原则的能力,着重强调了人类自由在实践、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存在。
所有后世的哲学家都必须面对康德的哥白尼转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康德的先验哲学可谓哲学史的一个转折点。但这并不意味所有人都赞同康德,1800年前后,关于康德哲学的两个问题备受关注:第一个是“物自体”的地位问题。雅各比和舒尔茨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成问题的概念。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就无法进入康德先验哲学;而一旦进入,这个概念就无法维持下去。毕竟,《纯粹理性批判》认为,像因果关系这样的先天概念的有效性被严格限制在现象界,那么,物自体何以可能是现象的原因呢?第二个是关于人的问题: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用康德自己的比喻来说,人似乎是“两个世界的公民”。在现象世界中,即感性世界(自然)中,我们完全被因果律决定;而在本体(noumenal)世界中,即精神(Geist)的超感世界中,我们是绝对自由的。这个有些分裂的人的形象,同问题丛生的物自体一样,都令康德之后的哲学家心意难平。
在1794—1795年出版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费希特果断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在费希特看来,人们必须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立场之间做出选择,前者认为精神(我)由自然(非我)决定,后者认为自然(非我)由精神(我)决定。费希特果断地选择了唯心主义的立场。如此一来,他就不得不解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把自然作为精神的产物来体验,这何以可能?费希特的精彩回答是,常识认为自然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因为常识没有认识到自然是精神的无意识产物。哲学的任务是把这个过程带到意识中去。只有当“我”在思想和行动中完全吸收了“非我”,它才会实现自己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仍然忠于康德,因为像康德一样,费希特不认为这种人类自由的实现是既定的,相反,人类自由是有待完成的任务。
哲学不是孤立发展的。德国唯心论的崛起与1800年前后发生的许多其他文化发展相关。毫无疑问,当时对德国哲学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法国大革命,它在德国知识分子中唤起了一种革命精神。费希特对德国人实现自由的呼吁就是这种精神的最有力表达之一。然而,这种精神与当时封建社会的德国是冲突的。此外,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雅各宾派恐怖政治,使人们对实现人类自由的方式产生了怀疑。在这种哲学和社会政治背景下,我们必须对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进行定位。最初,谢林受到费希特的影响,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为费希特的唯心主义辩护。然而,在谢林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和生物学研究后,他很快就不能再接受费希特“自然只不过是精神产物”的观点。谢林认为,先验哲学研究的是精神在自然界中的表现方式,必须辅之以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即研究无意识的自然界如何逐渐发展为有意识的精神。在谢林看来,原始的“有限的自然”和“无限的精神”是同一的,由此,我们同样有理由从自然史的角度或从精神史的角度来理解世界。他在18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著作主要致力于自然史,而《先验唯心论体系》则涉及历史,或者正如他在书所说:“精神的奥德赛”。
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艺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再看一看康德哲学,特别是《判断力批判》。书中,康德试图弥合上述自然与自由之间的鸿沟,这是他前两部批判的结果,分别涉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判断力批判》的前半部分,康德试图使自然与自由统一起来,而艺术作品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尽管康德主要关注对自然的审美判断,但在分析的最后,在讨论艺术作品时,他称其为道德的象征。虽然艺术作品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同时它也表达了人的自由。一件美丽的艺术品协调了自然和自由,虽然它还没有成为现实,但用司汤达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幸福的承诺”,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实现的和谐和幸福的承诺。
弗里德里希-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席勒对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雅各宾派恐怖政治感到震惊,他试图解释其猛然崩塌的原因。在席勒看来,这种恐怖是由于他所说的感性冲动(我们的感性本性)和形式冲动(我们的理性精神)之间的不和谐。当两者中的一个占主导地位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异常。这两者只能通过第三种冲动来调和,席勒称之为“游戏冲动”。在他看来,游戏冲动实际上定义了人类的本质:“人只有在完全意义上是人的时候才会游戏,而他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是完全的人。”在席勒看来,游戏冲动是最基本的冲动,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把感觉冲动和形式冲动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导致了对美的体验,“美是从两种对立冲动的相互作用中、从两种对立原则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所以美的最高理想要在实在与形式的尽可能完善的结合与平衡里去寻找”。
在1800年前后的著作中,谢林融合了费希特的革命精神以及康德与席勒的“艺术是对未来幸福承诺”的观点,他在1796—1797的短文《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初的体系纲领》(Das lteste Systemprogramm)中已经表现出这种浪漫的审美主义,这篇短文可能是谢林在图宾根大学宿舍与荷尔德林和黑格尔合住时写的:
最后的理念是把一切协调一致的理念,这就是美的理念,美这个词是从更高一层的柏拉图的意义上来说的。我坚信,理性的最高方式是审美的方式,它涵盖所有的理念。只有在美之中,真与善才会亲如姐妹,因此,哲学家必须像诗人那样具有更多的审美的力量。没有审美感的哲学家是掉书袋哲学家。精神的哲学就是审美的哲学。没有审美感,人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富有精神的人,也根本无权充满人的精神去谈论历史。在此应该弄明白的是,那些根本无法领会理念的人究竟缺少的是什么——老实说,这些人只要一离开了图表和名册就会两眼漆黑。
这样一来,诗便获得了更高的尊严。不论在人类的开端还是在人类的目的地,诗都是人的女教师;所以,即使哲学、历史都不复存在了,诗也会独与余下的科学和艺术存在下去。
之所以认为这段文字是谢林写的,是因为几年后的《先验唯心论体系》读起来就像是对这些文字的阐释。《先验唯心论体系》是来自康德、费希特、席勒思想的精彩整合,更蕴含了谢林1798年就任耶拿教授时期受浪漫主义运动影响所形成的精神。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试图证明“无限精神的有意识活动”和“有限自然的无意识活动”的原始统一性,他称之为“绝对”。在绝对中,无限的精神和有限的自然是同一的,或者说,是无差异的。谢林在他的“同一哲学”中要厘清的基本问题是“绝对”。一旦我们试图用一个概念来把握“绝对”,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主体的对象,这就否认了作为“绝对”本质的“绝对性”。因此谢林认为,人类的精神无法接触绝对,但艺术作品则体现了“有限的自然”和“无限的精神”的统一。于是在《先验唯心论体系》最后,艺术被誉为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因为艺术作品是“无限性的有限表达”,它揭示了精神和自然都具有的创造性想象特征。
这种创造性才能就是使艺术做成不可能的事情的才能,即在有限的产品中消除无限的对立的才能。那种在发展的最初级次中是原始直观的东西,正是诗才,反过来说,我们称为诗才的东西,仅仅是在发展的最高级次中重复进行的创造性直观。在两种直观中进行活动的正是一种才能,正是使我们能够思考与综合矛盾事物的唯一才能——想象力。因此,也正是同一种活动的产物,在意识彼岸我们觉得是现实的产物,在意识此岸则觉得是理想的产物或艺术世界。
我们所谓的自然界,就是一部写在神奇奥秘、严加封存、无人知晓的书卷里的诗。
谢林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阐述的立场被称为“审美绝对主义”,它可以被视为浪漫主义哲学的亮点之一。在西方哲学的漫长历史中,谢林是第一个将艺术置于哲学之上的人。
如果美感直观不过是业已变得客观的先验直观,则显然可知,艺术是哲学的唯一真实而又永恒的工具和证书,这个证书总是不断重新确证哲学无法从外部表示的东西,即行动和创造中的无意识事物及其与有意识事物的原始同一性。正因为如此,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好像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在这里,在永恒的、原始的统一中,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和必须永远在生命、行动与思维里躲避的东西仿佛都燃烧成了一道火焰。哲学家关于自然界人为地构成的见解,对艺术来说是原始的、天然的见解。
这种“有限的自然”和“无限的精神”的崇高统一,其表现方式之一就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一种无意识的无限性(自然和自由的综合)”。谢林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解释可以穷尽作品的意义,能够做的只是一系列无限的解释和再解释,这种观点有些类似于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但正因此,艺术作品以一种有限的方式表达了绝对性。
二、文明在游戏中生长,并作为游戏存在
从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中的形而上学、宗教问题和浪漫主义美学,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的著作《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似乎还有一段理论距离。《游戏的人》于1938年以荷兰文首次出版,通常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游戏学(ludology)和游戏研究的创始文本之一。沃伦-莫特(Warren Motte)2009年在《新文学史》上的文章中,甚至称其为“关于游戏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者声明”,“这本书极具启发性,以令人钦佩的广阔视野,第一个提出了成熟的鲁迪学理论,而且在初版的70年后,它仍然是‘严肃’的游戏讨论的必备参考书”。领域内许多著作开始引用赫伊津哈在书中第一章为游戏下的著名定义,或至少也多少提到过。
但细读的话,就会感受到该书与文章前面所谈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游戏的人》中其实可以发现很多浪漫主义世界观的表达。标题似乎就已经指向了席勒关于游戏冲动在人类生活中关键作用的思考;而在赫伊津哈给出的游戏定义中,与席勒一样,强调游戏是人类自由的表达。
如果要总结游戏的形式特征,我们不妨称之为一种自由的活动:有意识脱离平常生活并使之“不严肃”,同时又使游戏人全身心投入、忘乎所以地活动。游戏和物质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游戏人不能从中获利。游戏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展开,遵守固定的规则,井然有序。游戏促进社群的形成,游戏的社群往往笼罩着神秘的气氛,游戏人往往要乔装打扮或戴上面具,以示自己有别于一般的世人。
此外,赫伊津哈从不掩饰与浪漫主义运动及其美学的理论关系。早在其就职演说《历史表述中的审美元素》中,赫伊津哈就表明了与浪漫主义运动的理论关系,在《游戏的人》中他进一步表示:“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浪漫主义在游戏中诞生,这是文学和历史上的事实。”
然而,为了弄清《游戏的人》和《先验唯心论体系》之间的深刻联系,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更重要的是,因为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提出的如此有冲击力的论点并没有被所有读者理解,这不仅因为许多学者并未真正读过它,而且还因为其英译本有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从该书的副标题就开始了。英译本1949年由Routledge & Keagan Paul在伦敦首次出版,并从1950年起由波士顿的Beacon Press多次再版,副标题是 “文化中的游戏元素研究”(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然而,如果我们逐字按荷兰文翻译,译文应该是 “对文化游戏元素的研究”(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of culture)。那些将书名与内容对比着读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这些错误,至少是书名中的,而赫伊津哈本人在1945年去世前不久为英文版写的前言中也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在这篇前言中,赫伊津哈说他在苏黎世、维也纳和伦敦做《游戏的人》讲座时,每次演讲题目“文化的游戏元素”(The Play Element of Culture)都会遭到主办人的反对,每次的主办人都想把它改成 “文化中”(in culture),而每次他都不同意并坚持用属词of,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要确定游戏在文化其他表现形式中的地位,而是要确定“文化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游戏的特征”。奇怪的是,赫伊津哈的抗议都没被采纳。这个副标题的翻译错误完全掩盖了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提出的新锐主张,即“文明在游戏中生长,并作为游戏存在”。在倒数第二章“西方文明——亚鲁迪”中,赫伊津哈总结如下:
游戏因素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极其活跃,而且它还产生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作为一种社会冲动,游戏性质的竞赛精神比文化的历史还要悠久,而且像酵母一样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仪式在神圣的游戏中成长;诗歌在游戏中诞生,在游戏中得到滋养;音乐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在宗教竞争的语言和形式中得以表达。战争的规则、高尚生活的习俗,全都建立在游戏模式之上。因此,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论断:早期的文明是游戏。文明不是像婴儿出自母体那样从游戏中产生,文明在游戏中生长,它本为游戏,且从未离开游戏。
可见,赫伊津哈提出了一种具有冲击力的文化游戏本体论,使游戏现象成为理解文化基本结构的关键。与浪漫主义者一样,赫伊津哈将自然领域从自由领域区分出来,在这里,自然领域是由“物理的必要性”和“日常生活的必要性和严肃性”定义的世界。席勒和谢林认为艺术(被理解为我们游戏冲动的表达)是能够协调自然和自由的领域,赫伊津哈则认为游戏是自然和自由和谐的领域,与席勒一样,他也认为游戏是艺术的基础;谢林和席勒等浪漫主义者渴求生活从根本上审美化,而赫伊津哈则主张生活的鲁迪化。
初一看,二者间有重要区别: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生活的审美化是关于未来的工作,而对于赫伊津哈来说,审美化正逐渐成为过去的事情。尽管赫伊津哈强调所有的文化都“在游戏中生长,并作为游戏而生长”,但他并没有说文化总是处于游戏的状态。恰恰相反,与斯宾格勒1918—1923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悲观论调相呼应,赫伊津哈认为,文化总是在游戏中不断发展,文化在早期是最具游戏性的,随着它们的成熟,会逐渐变得更严肃,失去游戏的心态。对赫伊津哈来说,浪漫主义是西方文化中最后一个仍然具有游戏精神的阶段,到了19世纪,“似乎没有给游戏留下什么空间”。而该书最后一章在论及20世纪文化的游戏元素时,观点尤为灰暗,赫伊津哈指出文化的游戏元素“正在减弱”,“今天的文明不再是游戏”。
这一点在他对战争的分析中尤为明显,赫伊津哈用了整整一章来分析战争与游戏的关系。就像文化的其他表现形式一样,战争被认为是对自然的游戏性驯化。而在自然状态下,冲突(在这里我们感受到霍布斯《利维坦》的思想)可能很容易导致无休止的野蛮暴力,而游戏冲动将这些冲突转化为遵守规则的战争,此时“战斗作为一种文化功能”,“总是以限制性规则为前提,而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对其游戏性质的确认”。这就把“战争状态(那种正式宣战的)从和平和犯罪暴力中分离出来”。尽管赫伊津哈承认游戏作为人类的自由在自然界的表达,可能是暴力的(战争可能是最明显的案例,但肯定不是唯一的),但他明确地将其与作为自然状态特征的过度暴力区分开来。不是暴力本身,而是对暴力的无限使用才是自然状态的特征。然而,根据赫伊津哈的说法,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这种自然状态的回归。在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时,赫伊津哈说:“一战留下了‘全面战争’(total war)理论,驱逐了战争的文化功能,并消灭了游戏元素的最后残余”。在这里,他呼应了谢林在《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1809)中的后启蒙现实主义思想。谢林在书中强调,真正的、活生生的自由是选择好、坏的能力。尽管谢林和赫伊津哈在实现幸福和谐的时间问题上有分歧(一方认为那是未来实现的东西,另一方认为那是过去的东西),但他们在破坏和谐的原因上观点是一致的,即理论理性以及由之而来的技术理性、工具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大行其道。谢林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叹道:“对于外在目的的这种独立性产生了艺术的神圣性与纯洁性。艺术是很神圣、很纯洁的,以致艺术不仅完全与真正的野蛮人向艺术所渴求的一切单纯感官享受的东西断绝了关系,与唯有那个是人类精神对经济发明作出最大努力的时代才能向艺术索求的实用有益的东西断绝了关系。”
赫伊津哈也指出“独立于文化本身的外部因素”导致了游戏性文化的衰败。他特别提到了全球性的文化商业化,表现为商业稚态(puerilism),一种青春期和野蛮的混合体,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在全世界都很猖獗,“由现代通信技术引起或支持”,“技术、广告和宣传到处都在,促生竞争意识,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提供多种使大众商业满足的方式。当然,商业竞争不属于自古以来的神圣游戏形式”。
在谢林和赫伊津哈的作品中,这种对工具理性和技术的厌恶似乎使他们的世界观呈现出奇怪的矛盾。谢林的艺术哲学认为艺术作品可以体现出绝对,而工具理性和技术的产物不属于绝对(这对于认真行使其绝对性的“绝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艺术作品作为“哲学的真正官能”,它同时却产生一种完全客观的体验,这有点康德哲学的意味。
就赫伊津哈而言,尽管他宣称“文化生长于游戏,它本为游戏,且从未离开过游戏”,但他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没有游戏的言论,似乎缩小了其文化概念,从而引起重重矛盾。尽管赫伊津哈多次强调文化只有在“游戏中且作为游戏”(in and as play)才是可能的,但《游戏的人》一书中的一些文字,比如前面引用的游戏定义,又认为游戏完全发生在日常生活之外,只是“无足轻重的插曲”;再如虽然他认为游戏“对于社群的福祉不可或缺,是重要见解和社会发展的源泉”,但它同时也只是假装的,是“虚构的”,因此对现实生活来说是不重要的;再如其现实性使我们在一本正经地游戏,然而我们的游戏又完全不是认真的,也没有意义。
在《游戏性身份:数字媒体文化的鲁迪化》一书的导言中,我已经提出应该努力克服(在态度层面)游戏与严肃之间、(在本体论层面)克服游戏与现实之间尖锐的现代主义对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谢林的审美绝对主义和赫伊津哈的鲁迪绝对主义(ludic absolutism)(指他用游戏统摄人和世界亚鲁迪模式的尝试)才能站得住脚。参照Helmuth Plessner、Gregory Bateson,特别是Eugen Fink的《作为世界象征的游戏》(1960)一书,我尝试提出一种观点,即把游戏理解为一种双重存在现象。游戏与其说是完全在日常现实之外的空间和时间秩序,不如说是在游戏中附加于现实的意义。或者用谢林理论的术语:游戏的永恒循环、无尽重复,体现了有限的自然和无限的精神的统一。
因此,在我们的技术时代,我们不应该试图在作为主导的技术领域之外寻找这种有限的自然和无限的精神的统一,而应在技术本身中寻找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游戏是理解和建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关键特征,由此,计算机游戏可以被视为21世纪哲学的真正官能。
三、游戏化的图书馆和本体论
为了阐明和支持上述观点,我引入一个关键文本《巴别图书馆》,这将有助于理解我们这个技术世界里的游戏维度。《巴别图书馆》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1941年发表的一篇7页短篇小说,它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而且还被多次改编或转化为网络游戏。小说中第一句话就表明了博尔赫斯与谢林一样,满怀对无限性的浪漫主义情怀:“宇宙(别人称之为图书馆)是由数目不定的,也许是无限多的六边形组成的”:
在每个展室的中心是一个通风口,以低矮的栏杆为界。从任何一个六边形都可以看到上面和下面的楼层,一个接一个,无穷无尽。长廊的布置始终如一:20个书架,每边5个,排列在六边形的4个边上;书架的高度,从地面到天花板,几乎不超过一个普通图书管理员的身高。六边形的一个自由边通向一个狭窄的前庭,而前庭又通向另一个长廊,与第一个长廊相同,事实上所有长廊都相同。在前庭的左右两边有两个小隔间。一个是用来睡觉的,直立的;另一个用来盥洗。通过这个空间,也有一个螺旋形的楼梯,它向上和向下蜿蜒到最遥远的地方。在前庭有一面镜子,它忠实地复制了镜外的景象。
如果我们试图将巴别图书馆形象化,它看起来会是这样的,当然这只是图书馆的一小部分,因为六边形展室的数量是“不确定的,也许是无限的”。
每个六边形里的内容都与其他六边形相似,包含固定数量、尺寸相同的书籍。每个六边形的墙上都有5个书架,每个书架上有32本格式相同的书,每本书410页,每页40行,每行大约80个黑字。故事的叙述者说,巴别图书馆的居民一直对图书馆里的书感到困惑,因为它们的内容和顺序似乎完全是随机的。绝大多数的书充满了无意义的字母串,只偶尔会出现一个认识的单词。然而,大约500年前,一位天才的图书管理员发现了图书馆的秘密:
这位哲学家观察到,所有的书,无论它们之间有多大差别,都由相同的元素组成:空格、句号、逗号和22个字母。他还提出了一个后来被所有旅行者都证实的事实。在整个图书馆中,没有两本相同的书。从这些无可争议的前提中,图书管理员推断出图书馆是“整体的”——完美的、完整的、全部的,而且它的书架包含了22个正字符号的所有可能组合(这个数字虽然庞大得难以想象,但并不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能够通过某一种语言被表达出来。
根据叙述者的精彩解释,书的内容简直是囊括一切的。当我们试图设想巴别图书馆的图书总量时,面对的将会是一个组合爆炸数字。鉴于每本书包含410页,每页40行,每行80个黑字,每本书就包含1 312 000个符号。由于有25个不同的字符,这意味着图书总量是251,312,000。这是一个超天文数字,与此相比,宇宙中的原子数量(物理学家估计大约为1080个)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仅仅一本书,加上它的副本中,如果某个字母出现1—12个印刷错误,那么这个数字就比宇宙中的原子数量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巴别图书馆在物理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我们能够在每个亚原子粒子中放入一本书,宇宙中也只能存储巴别图书馆的极少一部分书籍。
如果用谢林的理论来表述,就可以说博尔赫斯的这个短篇小说以两种方式完成了关于无限的有限表达,所以居功至伟。一方面,故事吸引了无尽的阐释,关于《巴别图书馆》的二级文献已经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数学家布洛赫甚至基于这个短篇故事写了《难以想象的博尔赫斯数学》一书;另一方面,故事的主题唤起了,或者说几乎触及了无限性问题。
之所以说“几乎触及了无限性问题”,是因为即便是超天文数字,书的数量仍然是有限的,就像图书馆本身一样。根据叙述者的说法,图书馆是“无限的,但却是周期性的。假若一个步履不停的旅人随心而行,若干个世纪后他将发现,同样的书卷在同样的无序中重复,这种无序的重复,就成为秩序”。
之所以会重复,是因为图书馆像地球或整个宇宙一样是球形的:“图书馆是一个球体,任何一个六边形都可以是球体的中心,其周长是无法计算的。”事实上,巴别图书馆是尼采 “同一物的永恒轮回 ”思想的空间表现。假设宇宙中原子数量和它们在分子中的可能组合数是有限的,尼采认为在无限的时间内,原子就会出现所有可能的组合,从而最终重复自己,宇宙也会随之重复。当然,在尼采之前,早已出现这种宇宙循环、重复的思想,例如佛教和印度教的“时间之轮”以及轮回思想。而在西方,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如赫拉克利特那里也有类似表达,他认为宇宙每一万年就会自我更新。有趣的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这种想法已经与游戏本体论密切相关,因为他推测“世界的进程就是一个嬉闹的孩子在棋盘上挪动棋子,孩子是宇宙的绝对支配者”。
尽管《巴别图书馆》讲述的是一个具有游戏感的故事,但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戏剧或游戏。在互联网上,有一些关于巴别图书馆的计算机模拟(如https://libraryofbabelinfo/)。这些模拟惟妙惟肖,它们使用户能够访问博尔赫斯图书馆的每一卷书,人们可以随机地打开一本书,或者搜索特定的词和字符串,比如我这篇文章的选题。
如果按前文分析的,图书馆中书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宇宙中的原子数,那么在模拟图书馆中可以接触其中所有书籍的说法似乎就不可信。但这个巴别图书馆模拟器中的书籍并不是存储在硬盘上,而是基于动态创建(随机的或基于特定的搜索操作)。而且,用户每次最多只能保存30本书。否则很快服务器的硬盘、世界上所有的硬盘,最后整个宇宙都会被图书馆的一部分(仍然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填满。实际上,巴别图书馆的计算机模拟是一个数据库,这个巴别数据库确实包含了图书馆的所有书籍,但只是以一种虚拟的方式,作为一种可能性。因此,它不过是对(几乎)无限的有限表达,它使用户能够以无限的方式穿越图书馆。
博尔赫斯的故事和基于这个故事的模拟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是因为它们以一种非常贴切的方式表达了计算机时代的世界观。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详细解释的那样,“在一个计算机成为最重要工具的世界里,一切都变成了数据库”。 例如,当我们思考生命科学时,生命已经成为一个基因数据库(基因库),每个人都是基因数据库中的特定路径。就像巴别图书馆一样,“生命之书”一样的数据库显示了超天文数字的可能重组。如果我们意识到仅人类基因组就由大约30亿个核苷酸组成,用四字母语言书写,我们就会意识到,人类基因组的可能(重新)组合(43,000,000,000)的数量比博尔赫斯图书馆中的书籍数量要大得多,意义也重大得多。
在计算机时代,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已经从对现实的特定状态的静态表述,变成了一种游戏性的动态模拟。科学已经变成了模态(modal),因为它主要关注的不再是现实,而是可能性。或者,正如海德格尔在《时间与存在》中表达的那样:“可能性高于现实性”。正如博尔赫斯对所有可能的书籍的穷举引发了对巴别图书馆的想象模拟,计算机模拟不仅能够模拟现实,还能模拟多种可能的过去和未来。而且,正如基因改造等技术所显示的,这些模拟对可能世界的现实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就像巴别图书馆的模拟可以创造所有可能的书一样,生物技术原则上可以创造所有可能的基因修改。在计算机模拟中,宇宙的“几乎无限”特性得到了最为崇高的有限表达。
本体与文化其他部分发展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想想法国大革命之后,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经济和地理流动性的增加。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人是“被抛入人世间”(thrown projects)的,我们一生中去实现那些生命中的可行性,并不是从零开始的,从被抛入人世间,一个人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性别、种族、性格都是他探寻可能性的起点。在封建时代,关于“被抛入人世间”的重点是第一个词(被抛);而现代性关注的重点转移到“被抛的境况”。正如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的主人公乌尔里希所表达的那样,以往,拥有 “现实感”是有用的;而现在,我们应该关注 “可能性”。
尽管计算机游戏只是众多模拟中的一种具体类型,但它们可以被称为哲学的真正工具,因为它们以最纯粹的形式表达了计算机时代的游戏本体论。然而在现实中,严肃和非严肃游戏的划分并不绝对,比如《美国陆军》中坦克游戏引擎的模拟,也被用于士兵的实战操练。
最后要阐明的是,我们说游戏本体论是计算机时代的特点,并不是说这会使世界变得更好。正如谢林和赫伊津哈所说,游戏可以非常残酷。而作为人类自由的表达,游戏可以出入我们的闲暇时间,既可以精妙万分,也可以破坏力十足。游戏和工作、自由和力量,在计算机时代以最难以拆解的方式纠缠在一起。这种游戏性身份的诱惑性特征也会导致游戏成瘾的暴力。此外,正如博尔赫斯故事所表明,知道巴别图书馆的秘密并不能打开通往幸福的道路。叙述者解释说,聪明的人意识到,关于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所有可能真理都可以在图书馆的某个地方找到,但对于我们有限的生命来说,在这个超天文数字的图书馆中找到一本有意义的书的几率,却是超天文数字般地小。于是,最初那种发现图书馆秘密的欣喜,随之就变为严重的抑郁。
写作本文时,这令人沮丧的事实又强压心头。我知道,在巴别图书馆的某个地方,这篇文章的完美版本正等着我,但找到这个完美版本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把它当作一个搜索项输入。我也试着这么做了,但如你们所见,我的搜索结果只是文章现在的样子。最后我只能表达与博尔赫斯故事中的叙述者在解释图书馆构造时相同的浪漫希望:
在门厅有一面镜子,它忠实地复制了镜外的景象。人们常常从这面镜子中推断出图书馆不是无限的。如果它是无限的,那还需要那种虚幻的复制吗?我更愿意梦想,抛光的表面是无限的形象和承诺……




 Vanaf de derde druk verschijnt
Vanaf de derde druk verschijnt